米乐m6:音乐选秀节目历经数十年发展,已成我国电视娱乐节目的主流。本文借用符号学理论对我国音乐选秀节目展开宏观整体分析,认为其表意模式历经以专业化为标志的隐喻阶段、以大众化为标志的转喻阶段、以类型化为标志的提喻阶段、以游戏化为标志的反讽阶段的四体演进过程米乐m6,并对音乐选秀节目在反讽之后的走向进行探讨。
音乐选秀节目,是一种将音乐演出和电视真人秀深度融合的娱乐节目,它通常以电视为传播载体,以音乐为表现内容,通过歌唱比赛选拔音乐人才,并全程记录比赛过程。
若把音乐选秀节目视作一个跨媒介的符号系统,那么它的意义建构至少包含两层符号活动:一是音乐,是其符号表意的基本方式;二是真人秀,是其表意机制的内在逻辑。音乐,如同人类之语言,是经由听觉渠道传播的声音信息。作为一个传播过程,音乐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必然存在一整套共享的编码与解码规则。音乐符号的意义建构深受编码方式的影响,因此在音乐选秀节目中常常可见一系列节目制作者精心打造的符号编码策略,如歌曲选择、歌手形象、现场布置、广告宣传等等。与此同时,受众的解码行为也是决定音乐符号表意的关键因素,如霍尔所指出,受众会根据自身想法对信息进行抵抗式解码,具体表现为拉票、集资、应援等各种粉丝活动。在一个普通音乐文本中,歌曲文本身份是意义建构的关键。但在音乐选秀节目中,音乐虽是表意基础,却不是其唯一的“定调媒介”,甚至原本的伴随文本,如选手文本身份,会上升为主文本。以《我是歌手》为例,这档节目每期110分钟,但其中真正的音乐表演时长几乎不超过40分钟,剩下时间都是各种伴随文本的展示:幕后故事、筹备过程、亲友拉票等等。这种“喧宾夺主”现象由于电视成为音乐符号的媒介载体、视觉图像的加入而出现,并随着真人秀模式的引入而变得很常见。电视真人秀通过语言、视觉和声音符号共同实现意义建构。虽然名为真人秀,但它的表意目的并不在于展现“客观真实”,而是在符号化的拟态环境之中,基于各种社会文化预设和受众期待,精心打造一个令人信服的“媒介真实”,或者说“符号真实”。因此作为一个音乐文本,音乐选秀节目是由歌曲演唱(音乐)和真人秀(媒介化的空间)双文本组合构成的全文本。观众需要对音乐和真人秀进行联合解读,才能提取整体性的意义。
自1984年《青年歌手大赛》诞生以来,音乐选秀节目已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电视娱乐节目的主流。其娱乐性和观赏性强,受众广泛,无论收视率、流行度、还是影响力都非常可观。个别节目如《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等甚至成为现象级的媒体事件。从2004年开始,全国各大卫视推出了40多档音乐选秀节目。然而节目扎堆涌现,优质作品却不多,内容同质化现象严重。为了提高收视率,一些节目将焦点从音乐本身转向了煽情故事或插科打诨,节目内容呈泛娱乐化状态,导致音乐性缺失,且少有选手能真正通过选秀进入音乐市场,背离了选拔音乐人才的初衷。自2011年各大卫视开始引入国外版权之后,全盘模仿和抄袭现象频发,使独立和原创成分被进一步稀释,甚至出现为达所谓舞台效果而不允许演唱原创歌曲的情况,更遑论本土化模式的探索。
为什么会出现以上现象?一方面,作为一种文化商品,音乐选秀节目不是纯粹的艺术活动,而是典型的符号消费。符号消费的盛行既是当代消费社会的典型特征,也是音乐文化产业制造“流行”的结果。流行建立在广泛的集体认同之上,而偶像崇拜是获取认同的便捷手段。为了达到流行目的,当代音乐文化产业普遍采取以歌手为中心的策略。于是,音乐选秀节目作为当代流行音乐传播的重要平台之一,从创意、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都被有预设的编码,并紧紧围绕歌手的形象符号和消费价值而运转。另一方面,音乐选秀节目的娱乐成分越来越重,而音乐性和原创性越来越低,这其实绝非偶然,而是任何一种表意形式必然经历的发展历程,也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四体演进过程。
四体演进被认为是人类历史、文化、世界观演进的一般规律。在若干学者关于历史、世界观、文学、儿童心理发展、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等诸多领域的分析中都可见其身影。宋代邵雍在《皇极经世》中以四季之说把中国史分为皇、帝、王、霸四个时期,“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春、夏、秋、冬,昊天之时也。”(赵毅衡,2012,p. 216) 18世纪意大利启蒙思想家维柯把这种四元概念运用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分析中,将世界历史划分为神祗时期、英雄时期、人的时期、颓废时期等四个阶段,并指出各个民族都是按照这四个时代的划分向前发展,如潮涨潮落一般周而复始。美国著名修辞学家伯克在此基础上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四大修辞格,即比喻、转喻、提喻、反讽。在伯克看来,四大修辞格不仅具有修辞学上的意义,还是发现真理、描述真理的方法,在人类生活中具有关键作用。加拿大文学批判家弗莱在《批判的解剖》中进一步发展维柯的思想,将西方文学的叙述结构与四季更迭对应起来,指出西方文学的发展总是从神话开端,然后相继转化成喜剧、浪漫传奇、悲剧,最后演变为反讽。
我国符号学家赵毅衡则将以上关于历史、修辞、文学的演化规律应用到符号学,明确提出四体演化关系是符号表意形式的一般规律,符号文本总是从隐喻开始,然后到转喻、提喻、最后到反讽,形成一个意义关系的逐步分解过程。这一理论思想被不少学者运用到媒介研究之中。例如陆正兰《论音乐-空间文本》对音乐文本四种亚型变化的分析;王立新《视点下移与反讽转向:中国电视剧符号修辞演变批评》对中国电视剧影像话语的变迁史研究;饶广祥、朱昊赟《广告表意模式演变的符号修辞学分析》对广告表意模式四体演变轨迹的归纳等等。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证实,四体演进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表意演化模式。
比喻是表意方式的第一阶段,也是其他修辞格展开的基础。它利用另一事物来看待某一事物,以达到“此”中见“彼”,亦从“彼”中见“此”的效果。比喻包括明喻和隐喻,而影视符号通常以隐喻方式存在,因为它们无法使用“是”、“像”等连接词,而是借助像似根据性以建立喻体和喻旨之间的关联。与隐喻相对应的,是“神祗时代”。弗莱指出,在这一阶段,主人公在行动力和力量上均远高于凡人,就如同“神”落到了大地上。我国音乐选秀节目最初就呈现这样一种状态。
1984年,中央电视台开办《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简称《青歌赛》),成为我国音乐选秀节目的鼻祖。从赛制看,其规范性强。根据唱法不同,《青歌赛》分为民族、美声、通俗三个组别,又根据歌手的技能水平,分为专业组和业余组,考核内容除了歌唱水平还包括音乐知识和综合素养。从评定方式看,权威性高。《青歌赛》的评委无一例外是该组别的音乐专业人士,他们来自全国个大音乐学院、剧院、文工团、歌舞团,其中不乏知名作曲家、声乐教授、歌唱家、指挥家。从人才选拔看,《青歌赛》为音乐界输送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专业歌手,例如毛阿敏、宋祖英、、阎维文、张也、解晓东、林依伦等等。《青歌赛》就如同一场音乐领域的“神”之对决。对于普通人来说,专业歌手的存在是无比遥远、难以触及的,如同神明之于凡人一样。“神”本来存在于天上,只生活在音乐院校或歌舞剧院里,但是电视这一大众传媒将“神”带到了地上,使“神”的对决变得可观、可赏,给了普通观众以仰望的机会。但是也仅限于欣赏的层面,因为无论是歌手的选拔、赛制的安排、还是比赛的结果,都不是普通观众可以左右或参与的。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音乐选秀节目只专注于展现音乐性,体现精英意识形态的话语模式和审美主旨。
转喻建立在接近性与邻近性的基础之上,其基本策略是通过联想用相邻的一种事物替代另一种事物。例如丹宁布“denim”以原产城市“Nimes”为名,是用产地来指代产品的转喻做法;新闻报道基于媒介意图而进行的媒介选择,是以“媒介真实”代替“客观真实”的转喻做法。因此,转喻时常被等同于推理(reduction),意指一种关联性的类比。
与转喻阶段相对应的,是维柯的“英雄时期”。在英雄时期,贵族和平民截然分开,两者之间展开激烈的阶级斗争以争夺婚姻、土地所有权。随着90年代后期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产业的兴起,各个地方电视台争相举办地方性音乐比赛,使央视在文化传播上的垄断地位受到挑战,《青歌赛》造“神”的能力也被大大削弱。到2004年,湖南电视台的《超级女声》横空出世,开创了将国外真人秀模式引入音乐比赛的先河,完全颠覆了《青歌赛》为代表的专业歌手选拔传统。它以“海选”方式从大众中挑选参赛者,再以大众为评委,根据大众投票决定比赛结果。从赛制安排、歌手选拔、到评选方式都体现出前所未有的草根性,审美倾向也随之平民化。从《超级女声》等节目中脱颖而出的歌手,就如同“人间英雄”,他们的演唱水平虽然高于普通人,在行动力量上高于“凡人”,但由于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不具备专业的音乐素养,因此并不高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因而可以说是对“神明”(专业歌手)的高模仿。《超级女声》的巨大成功激发了诸如《快乐男声》、《加油,好男儿》、《绝对唱响》、《我型我show》等一大批草根选秀节目,这些节目使真人秀模式迅速成为电视娱乐节目的主流。而《青歌赛》等专业性音乐比赛却陷入叫好不叫座的窘境。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正是“平民”与“贵族”争夺权力的表现。
由此,音乐选秀节目进入到以大众化为标志的转喻阶段。大众文化时代和消费社会的到来逐渐改变了普通观众的地位。音乐不再是神圣的、精英的,而成为大众化、市场化的娱乐形式。以往隐藏在音乐符号背后的选手文本身份走上前台,成为文本的中心结构。选秀节目的符号意义由专业音乐符号下移到大众文化符号,确立了草根化的符号取向,“文本修辞方式因邻接新的时代话语而为之一变”(王立新,2012)。然而与草根节目的兴起相伴随的,是盲目跟风、投票黑幕、以及低俗内容的泛滥,国家广电总局不得不出台文件予以限制。这也暴露出音乐大众化之后必然面临的审美疲劳、品味下降等弊病。
提喻,相当于再现,是以局部替代整体,或以整体替代局部。几乎所有的图像影视都是提喻,因为它只能展现真实图景的某一部分。
此前的音乐选秀节目,无论是《青歌赛》还是《快乐女声》,选拔获胜者都是基于“神”的标准,即具备专业歌唱水平,同时亦具备成为明星的潜质,比如良好的相貌、外形、个性、年龄、社交能力等等。专业评委的投票具有左右比赛的关键意义,“神”的影响力很大。然而2012年推出的《中国好声音》却打破了这一定律。《中国好声音》以盲听、盲选的方式只关注歌手的“声音”,即歌唱水平,而不把考虑其他因素,采取了以部分替代整体的提喻手段。在这种运作模式下,形形的演唱者登上了电视荧屏。他们大多相貌普通、身材走样,有的是长期从事幕后工作的无名音乐人,比如姚贝娜、金志文、关喆、孟楠;有的是在其他比赛中被淘汰的失败者,比如徐海星、平安;有的则是声音太奇特、或者风格太冷门而找不到出路,比如吴莫愁等。相比《超级女声》近乎“神”的获胜者,《中国好声音》的歌手却有着各种缺陷,也被生活打击而失意,是与我们普通人无比接近的“凡人”。专业评委的文本身份也出现大幅度转变,从评定者变成了“导师”,成为选手的“仆从”,其投票也不再重要,“神”的权威受到极大挑战,甚至被拉下神坛。相反,场外观众的投票成为决定性因素,大众性进一步增强。于是,“人”代替“神”或者“英雄”,成为了故事的主人公,进入到维柯所说的“人的时代”。在此阶段,选手作为文本主人公既不高于普通人,也不高于所处的环境,同时主人公具有普遍人性因而能够激起普通人的强烈共鸣,这也正是《中国好声音》取得广泛认可的原因。
除了《中国好声音》之外,2012年-2013年之间还涌现出深圳卫视以无伴奏人声演出的《The Sing-off清唱团》、北京卫视主打和声重唱的《最美和声》、广西卫视改编传统民歌的《一声所爱·大地飞歌》、以及四川卫视的藏歌比赛《中国藏歌会》等等多档节目。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音乐选秀节目几乎无一例外的采用类型化的策略,以某一种音乐风格或类型为主打,是典型的提喻做法。音乐选秀节目从“大而全”走向了“少而精”,也标志着这类节目进入到真正的成熟阶段。
自2013年开始,《我是歌手》、《蒙面歌王》、《偶滴歌手》、《歌手是谁》、《金曲捞》等节目相继推出,意味着音乐选秀节目进入到以游戏化为标志的反讽阶段。
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反讽以某一事物的反面意义来解释该事物,是字面意义与实际意义相反的双重意义叙述。反讽通常包含三种符号意义,即意图意义、文本意义和解释意义,其中两两冲突即可形成反讽。维柯称反讽为“颓废时期”,是人的主体性上升、个人意识觉醒的繁荣时期,也是逐步走向没落、自私自利、道德沦丧的时期。伯克将反讽视为“对话性的冲突”,事物在辩证关系中互相转化和建构。弗莱将反讽视为冬天的叙事结构米乐m6,讲述神逝去后的世界,其基本意象是夜晚、黑暗、以及生命的解体。赵毅衡则认为反讽是对前面三种修辞格的总否定,是任何一种表意体裁演进的必然结局。
1、文本中充斥各种矛盾意义的符号。反讽文本总是存在对立的双层意义。以《蒙面歌王》、《偶滴歌手》、《歌手是谁》等节目为例,一般而言,歌手的辨识度是成名的关键因素之一,无论是声音、外形或性格,只有具备鲜明的个人特色才能从竞争中脱颖而出。但是这些节目却反其道而行之,要求参赛歌手通过服装、面具、变声器等各种方式将自己伪装起来,然后由评审和大众竞猜他是谁。谁能将身份悬念保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出者。选手一边竭尽全力将个人特点隐藏,一边又期望通过节目提高知名度。矛盾表意处处可见。
2、形成带有悲彩的宏观反讽。反讽一旦从语言扩展到符号,尤其是多媒介的符号系统,就从单层次表意变成复合层次表意,进入到宏观反讽。所谓宏观反讽是指:“符号表意不再局限于个别语句或个别符号的表意,而是整部作品、整个文化场景、甚至整个历史阶段的意义行为。”(赵毅衡,2011)《我是歌手》每一季邀请7位成名歌手参赛,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青歌赛》类似,都是专业歌手之间的对决,但实际上的参赛者都是早已出道的老歌手而非新秀。由“过气”歌手翻唱经典老歌(且大多还不能是自己的成名曲),最终目的却是想要获得“新生”,其主题思想无疑颇具悲情意味。与之类似的是江苏卫视2017年推出的《金曲捞》,将所谓“蒙尘老歌”再度包装推上舞台,同样试图通过“怀旧”打造“第二春”。于是我们看到,反讽在整个文本上发挥作用,矛盾冲突的双层意义同时体现在节目主旨、音乐风格或人物形象等多个层次。此时的反讽已超越原有的幽默、调侃等浅层次的表意需求,上升至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讨论。
3、音乐与空间独立表意。陆正兰指出,当文本在场性中音乐和空间的联系不复存在,两者各自保持独立性,就构成了反讽式文本。(2017) 在《我是歌手》、《蒙面歌王》等节目中,歌曲风格、演绎方式等音乐性的内容已经脱离了真人秀的叙事轨迹,不再对情节起到任何推动作用,如同“气氛音乐”一般,无法归入选秀文本组成之中。音乐与真人秀不再是统一文本的有机构成部分,而实现了各自的独自表意。
4、游戏成为首要目的,音乐则沦为游戏手段。《蒙面歌王》等节目以模仿、竞猜、悬念为卖点,从根本上背离了选拔音乐人才的初衷,转向于满足大众的好奇心和猎奇欲望。观众也只关心谁在唱歌,或者对伪装服饰津津乐道,却不再关心唱了什么又唱得如何。于是频繁出现糟糕的灯光音响、平庸的编曲水平、滑稽的演出形象、甚至对口型假唱等现象也就不足为奇。音乐选秀节目的符号表意活动已经变成一种所指优势下的“骗局”,其目的不是传播音乐,而是以音乐为游戏手段提高收视率,音乐本身则被解构、被边缘化了。
反讽在音乐选秀节目中的广泛运用,实际上反映出整个文化领域的泛娱乐化趋势。如饶广祥所指出,娱乐化培养了大众的阅读趣味,接收者更倾向于接收“有趣味性”的媒介文本,反讽于是成为主流格局。(2013) 费斯克有关受众快感的理论从另一个角度对娱乐至上进行了解释。他指出,受众是电视文本的主动参与者,他们总是根据自身的社会经验进行狂欢式的快感生产,并与文本发出者,或者说主流意识形态,争夺意义控制权。受众“抵抗式阅读”的的主要手段就是“打破既有规制、嘲讽权威、把玩文化政治游戏”(蔡骐,欧阳菁,2006)。可以说,反讽已经从语言层面的一种修辞手法,扩展成为当代文学艺术的主要叙述方式、一种主导性的文化策略、甚至是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组成方式。
那么反讽之后,音乐选秀节目又将走向何方?维柯的历史循环论认为,人类历史从神的文明时代逐渐衰败和解体,最终来到颓废的混乱时代,当一个从神、英雄、人、到颓废的周期结束后,将开始第二轮的四阶段循环。但是这种周期循环不是机械式的复演,而是不断变动、发展与更新的。它同时包含进步与退化的内容,因为从神到人的历史演进中,既有物质的逐渐丰盛和理性的上升,也有道德的堕落和创造力的衰退。弗莱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西方文学从隐喻到达反讽之后,会向神话回流,重新开始新一轮的四体演进。但赵毅衡却认为弗莱的看法过于乐观。他指出,一旦某种表意形式走到反讽就只能终结,重新开头的将是另一种表意形式。但他同时也指出,反讽并不是自我毁灭的尽头,反而意味着前景与出路,它在颠覆既有表意形式的同时,也积极催生新的表意形式。
2017-2018年,除了少数几个老牌节目的回归,音乐选秀节目市场还涌现出几档全新节目,并且一面世即引发现象级热议。其中包括首次将地下说唱带入大众视野的《中国有嘻哈》、掀起粉丝造星运动新高潮的《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这些节目引入了嘻哈音乐、偶像团体等新的音乐符号分节,使音乐选秀节目的符号细密度增加,受众进一步细分,对象全域随之扩大。这些节目的参赛者均是来自相关领域的音乐专业人士,而非普通大众,原创歌曲也占据很大比例,似乎暗示着音乐选秀节目正如维柯、弗莱所认为的一般周而复始、开始向专业化阶段回流。但从运作模式看,它们从国外引入版权并完全复刻其节目设置,依然以观众投票决定胜负且权重之高前所未见;从音乐文本看,对音乐本身的关注虽然高于《蒙面歌王》等节目,但选手文本身份依然是绝对的“定调媒介”,节目不断通过幕后故事、现场花絮、日常跟拍等各种手段打造文本身份认同;从叙事结构看,它们不采用线性连贯的叙述,叙事镜头在音乐演出、幕后花絮之间反复切换,形成明显的叙事裂痕。以上种种都与《青歌赛》这类专业音乐比赛有很大区别。
可见,这些节目是以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阶段的、新的表意形式在向前演化。这是否可以视为一种新的表意形式、是否会成为音乐选秀节目的整体转向尚需时日证明,但毋庸置疑的是,参与文本意义编织的主体变得越来越多元,受众社群内在认同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音乐选秀节目从以专业歌手对决为标志的“神祗时期”开始,历经大众化、类型化阶段,滑向了游戏化、娱乐化的反讽阶段。符号修辞的演进与时代变迁密切相关,音乐选秀节目的快速生发与衰落正是当代浮躁不安的娱乐文化的一个缩影。音乐选秀节目或将开始新一轮从隐喻到反讽的模式演化。如柯林武德所说:“历史决不会重演它本身,而是以一种有别于已成为过去事情的形式而出现于每个新阶段。”(1986,p. 27)那么这一次,意义阐释权被受众社群深度掌控(例如场外粉丝在王菊事件中展现的强大力量),或许会成为新一轮音乐选秀节目表意活动的新质素。
柯林武德, R.G. (1986). 历史的观念(何兆武, 张文杰,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谢杨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西南科技大学文艺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化与传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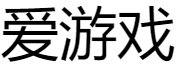 爱游戏体育
爱游戏体育